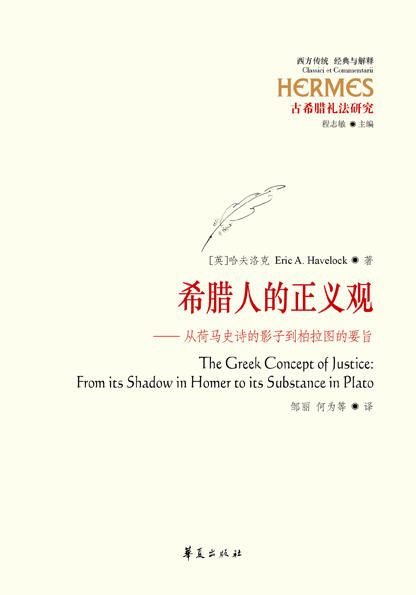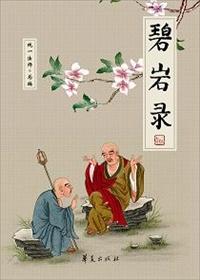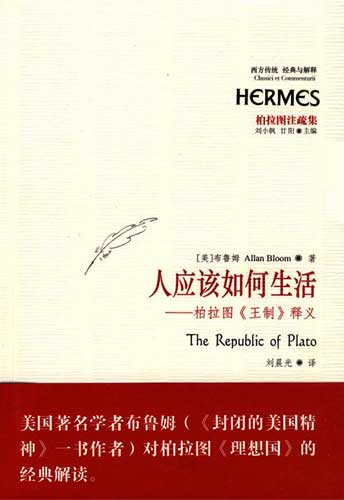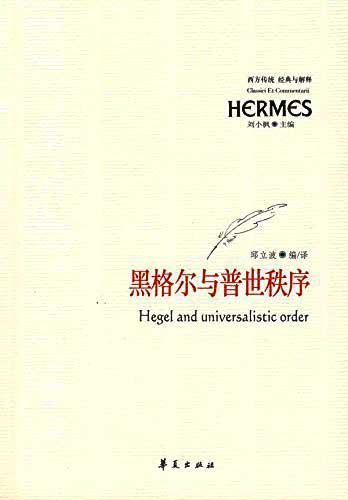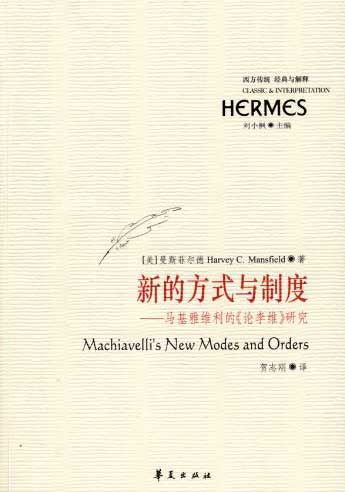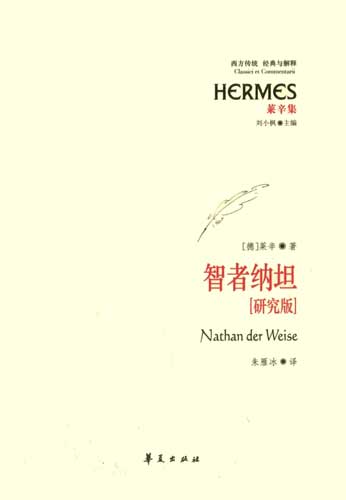图书详情
章节目录
中译本说明
自序
前言
第一章 从荷马到柏拉图
第二章 史诗在无文字社会中的功能
第三章 韵律记忆的心理
第四章 荷马叙述的社会
第五章 荷马式想象中的一些要素
第六章 荷马式储存的方式方法
第七章 《伊利亚特》中的正义
第八章 《奥德赛》中的合法性
第九章 《奥德赛》的道德观
第十章 《奥德赛》的正义
第十一章 赫西俄德的正义观
第十二章 口语和书面语
第十三章 动词to be早期史
第十四章 梭伦的正义观
第十五章 前苏格拉底的正义观
第十六章 埃斯库罗斯的正义观
第十七章 希罗多德的正义观
第十八章 柏拉图的正义观
第十九章 书面语的哲学
后记
参考文献
索引
作者简介
哈夫洛克(Eric A. Havelock,1903-1988)出生伦敦,求学于剑桥,二十年代移居加拿大,逐渐接受包括口头诗学和媒介交流等在内的现代理论,以此解读柏拉图与荷马,后来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代表作为《柏拉图绪论》。
编辑推荐
希腊思想家感兴趣的是礼法的来源、依据和目标等颇为抽象的问题,而不是“分权”、“监察”、“物权”、“继承”和“诉权”之类具体的礼法问题。希腊人往往更多地就制度、法理或立法精神展开辩论,他们看重“正义”和“公平”甚于“真假”和“对错”,更重“城邦的福祉”而非个人的自由。
哈夫洛克这本书最大的学术价值在于指明了“正义”等观念在古希腊时期的“内涵”,也就是“内向性的涵义”。哈夫洛克看到了古希腊思想中的内在化过程,人们的思想以及表达这种思想的概念或术语都有一个由外而内的发展历程:最先表示外在属性的词汇渐渐用来表示内在的品质。因此,与现代观念不同,正义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在的自律也是灵魂的真正内在德性。
书摘插图
序言
近代以来,西人即便在诗歌戏剧方面也从未“言必称希腊”,但在礼法方面,却往往“言必称罗马”:罗马政制和罗马法的确比古希腊礼法显得更为条理分明,而且也是西方现代制度和法学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城邦政制没有“法理学”(jurisprendence),实际上,在更为根本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方面,古希腊人比发明了res publica这一术语以及juris prudentia这一学科的罗马人有着远为丰厚的思想资源——这或许就是希腊与罗马巨大差异的一种缩影:在具体的实施技巧上,罗马人无与伦比,而在学理的深思明辨方面,希腊人则更胜一筹。
罗马人曾遣使“抄录希腊人的制度、习俗和法律”(李维语),虽非信史,亦属有自。但希腊礼法却远不及罗马法有名,甚至连希腊法律的研究者也怀疑“希腊法律”之说是否成立。其实,古希腊思想家感兴趣的是礼法的来源、依据和目标等颇为抽象的问题,而不是“分权”、“监察”、“物权”、“继承”和“诉权”之类具体的礼法问题。以法律为例,在庭审中,普通希腊人往往更多就制度、法理或立法精神展开辩论,看重“正义”和“公平”甚于“真假”和“对错”,更重“城邦的福祉”而非个人的自由。所以,希腊人十分重视礼法所带来的“德性”、“幸福”和“美好生活”——这些更为根本的诉求在现代政治学和法学中几乎已踪迹全无矣,正所谓“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商君书·开塞》)。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德治不能取代法治,但离开了法理和德性,法律就变成了单纯的技术,不再有收拾人心、进德修业以求优良生存之鹄的。
与现代法学不同,古希腊法律思想与政治、宗教、哲学和伦理学联系十分紧密,“由最好的人来统治还是由最好的法律来统治更为有利”(《政治学》1286a8-9),诸如此类的元问题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考法学的出发点。古希腊“礼”、“法”密不可分,而法律的兴起与发达,本身就与民主政治互为因果:法律就是民主,或者说法律就是民之“主”。因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的“礼法”就成了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与政治、伦理和宗教交织在一起,所谓“编著之图籍”均可为“法”(韩非语),都是“城邦的纽带”(欧里庇得斯语)。
所幸近半个世纪以来,古希腊礼法研究在西方学界渐始蓬勃——这才是我们的法学理论界应该与国际接轨的地方之一。编译这套译丛,不为救世,不为解惑,惟求提醒。苟能“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则有益于我们远离空疏的自大和滑稽的空想。
书摘:
中译本说明
程志敏
哈夫洛克这本书看起来题目很大,不明就里的读者会以为它是整个古希腊的正义史论,研究正义观念的发生、发展、成熟、转意和终结,但实际上该书一大半篇幅都在讨论荷马史诗。其正标题“希腊人的正义观”和副标题“从荷马史诗的影迹到柏拉图的要旨”,似乎都有些名不副实:难道作者仅仅讨论了希腊正义论的“影子”?
尤为让人惊讶的是,该书没有专章讨论亚里士多德,全书仅有六次作为背景顺便提到这位“古希腊”的大师。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大量讨论“正义”,但《希腊人的正义观》却一次都没有引用或提及这部重要的正义论著作。全书正文结尾有一小段话总结“柏拉图之后的诗学”,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希腊诗歌评判方面可能不如柏拉图,因而他对乃师的批评很不公正。西方有不少学者说亚里士多德故意曲解前人,甚至“无中生有”解释老师的著作,所以,当我们听说其他人这样的评语:“亚里士多德无疑是西方最伟大的哲人之一,还曾在柏拉图身边生活达二十年之久,然而我们却看到,他常常异常激烈地反驳柏拉图,但往往又完全没有理解柏拉图”,我们对此不知道应该表示惊讶,还是感到气愤,甚或只有对此后思想发展的悲悯。
哈夫洛克故意忽视亚里士多德,也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既然几乎所有的篇幅都给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家及其作品(尤其荷马史诗),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然就无法过多涉及——专门讨论柏拉图正义观的篇幅还不及埃斯库罗斯(可能是因为哈夫洛克翻译和评注过他的作品)。哈夫洛克以柏拉图诗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柏拉图序论》,同样花了很多篇幅讨论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也同样很少谈到那位写过《论诗术》的作者亚里士多德!
这样的情形也许是因为哈夫洛克在学术上喜欢另辟蹊径以挑战传统,往往故作惊人之语,但效果总不大好——强调口头传播理论的多伦多学派影响不小,也误导了不少后生。《希腊人的正义观》大量使用oral及其相关词,因为他的理论资源就是口头诗学理论的创始人帕里,他称之为“口传风格的杰出学者”,哈夫洛克另外还写过一本讨论口传与书写关系的书。这都是多伦多传播学派理论上的共同爱好。
哈夫洛克的著作,尤其《希腊政治的自由气息》,遭到过施特劳斯详尽而深刻的痛批,说它“不是一般地糟糕”,施特劳斯因其“堕落的自由主义”而表示绝不宽容,并上升为这样的普遍评价:“学术本是文明社会用于防御野蛮的壁垒,却更经常成为回归野蛮时代的工具。”哈夫洛克在去世两周前的1988年3月16日,也就是施特劳斯去世15年以及上述批驳文章问世近30年后,发表了自己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柏拉图的政治学与美国宪法”,专门批评施特劳斯及其门徒(尤其布鲁姆)对柏拉图的阐释,并力挺波普尔的解读,在哈夫洛克看来,施特劳斯学派的方法不能把我们带回到柏拉图那里。
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的方法当然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古典思想的身处,同样,如果正确对待的话,哈夫洛克也能够把我们带回到那个他颇为熟悉的年代,毕竟这位古典学家在古希腊思想的研究中下过很深的工夫,在加拿大和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古典学系教书,担任杰出讲座教授。他与施特劳斯学派的恩怨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也无意于施特劳斯学派在美国曾经引起的激烈论战,我们去西方学者那里“留学”的目的不是看热闹,更不是充当哪一派的志愿军甚至雇佣军(更不用说文化殖民下的思想亡国奴了)——近现代中国的惨痛教训已成后事之师,我们的目的是学成归国,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只要有教于我,统统拿来。更何况良性的学术争论本身就是思想生产的有效机制,这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自然不值得深入纠缠。
我们既没有必要把哈夫洛克捧得太高,把他与莱维纳斯、德里达相提并论,甚至还把他与尼采和海德格尔联系起来讨论,认为哈夫洛克在解读柏拉图著作尤其《斐德若斯》和《王制》方面有启迪之功;我们也没有必要彻底否认哈夫洛克的颇有学术价值的工作,尽管哈夫洛克这本《希腊人的正义观》试图以语言学而不是“语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概念,遭到过麦金太尔的批驳,但亦不乏高明之见,这本语言朴实、通俗流畅的专著,大量引用古典文本作为分析的材料,对于我们理解古人的思想,的确是一本非常不错的入门读物。
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该书学术价值的意图,恰恰相反,这种由很多大大小小的豆腐块札记式短论构成的书,比那些装模作样的高头讲章更让人觉得亲切,尤其符合现代的“微阅读”习惯。其简洁明快文风比那些靠堆砌术语(更不用说生造乖僻字样)来表现深度的现代学术著作来说,更容易吸引读者进入古典的世界,而不是用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把读者挡在门外。认真阅读就会发现,这本书其实并不“通俗”,仅仅从它专辟一章讲最高深的形而上学问题“存在”,就可见一斑。这对我国最近十多年热闹非凡至今不衰的“是”与“在”之争不无参考价值。
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力图以“希腊人的正义观”之名表明自己这本书的“希腊性”,也就是尽量维护古代思想的原貌,避免现代观念的干扰。哈夫洛克看到了正义问题的古今之异,也知道现代观念(如现代的神话概念)会把我们引入歧途。不过,他的现代路数可能让他的一些洞见大幅度缩水,变成仅有一定“学术”参考价值的资料汇编。哈夫洛克认识到:
实际上,古典研究近来已经意识到,希腊古风时期的思维意识与我们极为不同,它尤其意识到我们文化中所熟悉的道德责任观念在古希腊要么不存在,要么至少有着相异的表达。这样的看法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反驳,因为它一再断定,一种普遍的正义法则在古希腊思想中占有首要的地位。争辩双方或许都从各自的立场假设了与那个时代不相宜的问题。我们难以摆脱如下的习惯:寻找我们习惯了的事物消失的地方,或者相反重申它必定存在于那些地方。
这是哈夫洛克这本书的“结语”中的一段话(这个交代研究方法的“结语”其实应该是本书的“导言”)。哈夫洛克虽然看到了古今之异,也看到了很多现代问题对于那个时代来说“不相宜”,但他试图超越论辩双方,似乎显得不自量力,因而必然走到岔路上,终归为现代观念羁绊住了。
比如说,作者不认为荷马社会是一种“部族君主制”或“宗族王权”,其理由在于没有铁证表明那个时代曾存在过这样一种政体,因为那些统治者不是“君王”,而是tyrants(该词是现代人对希腊语tyrannos的“误译”),那时的含义是“城邦公民大会(agora)授权的大众领导者”。但哈夫洛克这样的理解实际上站在了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学者的对立面,因为“君主制”或“部族王权”公认为最初的政制形式,而荷马时代的政体就是这样一种由家长权力演变而来的统治模式。
哈夫洛克这本书最大的学术价值在于指明了“正义”等观念在古希腊时期的“内涵”,也就是“内向性的涵义”。哈夫洛克看到了古希腊思想中的内在化过程,人们的思想以及表达这种思想的概念或术语都有一个由外而内的发展历程:最先表示外在属性的词汇渐渐用来表示内在的品质。因此,与现代观念不同,正义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在的自律,也是灵魂的真正内在德性。
哈夫洛克认为这个内在化的过程在柏拉图那里得以完成,柏拉图“通过将正义作为一种灵魂中的‘德性’,并用这个词来象征人性,他完成了作为一种个人品质的正义的内在化”(页307)。在哈夫洛克看来,柏拉图甚至“鲁莽地”(incautiously)认为,灵魂内部的正义或正义的内在信仰,就已经足以解决一切问题(页216),这样的评价显然过头了。但正义的确如柏拉图(苏格拉底)所说(《王制》443c9-444a2),正义的“内在”(entos,王扬译作“内心”),在于“自己统治自己”,也就是自己管理自己,一切事物从“多”变为“一”,便井然有序(kosmesanta),它的本质就在于“节制”而“和谐”,这种美好而高贵的品质或精神状态(heksin,布鲁姆译作condition,王扬译作“精神和谐”)就是正义,而能够教导这种行为的知识就是智慧。
正义不仅是内在的品质,也是外向的行为。也许儒家“内圣”如何开出“外王”的千古难题在“正义”这个词的整全含义中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儒家《大学》“八目”过于浓缩的推导过程中不大容易理解的“欲…先…”和“而后”这两个逻辑界点,其实可以训作“德”,“德者,得也”,这里所说的“得”不是儒家古代经生所理解的内在收获,而是精神外化的现实成就。
所以,柏拉图所完成的内向“正义”论,主要还不是一种“理论”,而是“行动”。他所说的“道理”不是“正义”的哲学定义,尽管他用了“定义”一词,该词在这里却是“部分”或“阶层”之意。实际上,苏格拉底在整个《王制》多层次多结构的探讨中,早已表明,对于美好生活来说,任何逻辑上的定义都于事无补。苏格拉底虽然一上来就以克法洛斯的描述不合“定义”击退了这位可敬的长者,但自己后来接替克法洛斯成为谈话的“头儿”之后,却再也没有提到“正义”的“定义”(551a12和c2的horos仅仅“界定”具体的寡头制),他只是说,我们不能“一心扑在没有止境的物质追求上,跨过了人生基本需要的界限”。
“正义”本身是“德性”之一,而“德性”一词同样出现了含义内向化的过程。该词本来指物体(比如马匹)的优良特质(希罗多德《原史》3.88,西塞罗《论法律》1.45),后来才转而表示人的道德品质。这样的“德性”才是人应该有的“自然”,也就是内在的本性,否则阿奎那所谓“自然倾向”能够让我们判断好坏善恶(《神学大全》1.94)这一说法就显得毫无根据的武断,同时也失去了正确理解“自然法”的钥匙。
正义的内在性已经很难为现代人所理解,因为我们在高喊“自由”和“平等”等权利的时候,不知道这些东西本身不假外求,不需要用生命去换取,它们就在我们身上。柏拉图《王制》中的克法洛斯所说的“自由”,不是外向的政治权利,而是灵魂摆脱欲望的逍遥状态(329c;另参西塞罗《论老年》14.49),“自由”与“勇敢”和“审慎”一样,是内在克制之后的无所挂碍,像“自由人”一样,不受饮食男女和钱财富贵的统治。人因自由而宁静,生活才会美好(329a),与后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想不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的外在权利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远古至希腊逐渐实现的“内向化”成果被后世抛弃或反转了,又走回了“外向化”的道路,正如苏格拉底辛辛苦苦从天上拉下来的哲学又被后人送回了天上,与人世越来越没有关系,哲学就好像黑铁时代的“羞耻”和“报应”神,离开凡夫俗子,回到不朽的天神那里去了(赫西俄德《劳作与时令》行197-200)。所不同的是,哲学被送到天上,是为了取代诸神的位置。哲学是属人的理性产物,因此哲学上天就是人义论的胜利。哲学胜利,理性膨胀到为万物立法的程度,诸神退隐,宇宙中便再也没有羞耻(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还有“敬畏”之意),这样的僭越当然会遭到“报应”。
不管哈夫洛克出于何种目的,但他终归看到了哲学上升为“最高的音乐”或“文教之教主”(见柏拉图《斐冬》61a3-4)所带来的问题:“希腊从此就委身于一场危险而让人神魂颠倒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荷马笔下的英雄争斗已转变为概念、范畴和原则之间的战斗”。活生生的思想世界,在哲学一统天下的封闭世界中,变成了充满头盖骨的战场(黑格尔语),到处是“知性的尸体”和“概念的木乃伊”。
欧洲自此之后便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影子”中,几千年都使用着干瘪的语言,还用抽象的概念来交流和教学,而“荷马式的‘教化’不知不觉滑落成为往昔,变成一种记忆,而一旦如此,希腊人在古风和黄金古典时期所展现出来的特殊天才,也会变成一种回忆。”事实上,那些美好而异质的珍宝,的确已经变成凭吊的对象,渴望拯救的现代人已不能靠吟咏“只是当时已茫然”来打发日子:回归古典,也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哈夫洛克不是已经大致指出病根和相应的疗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