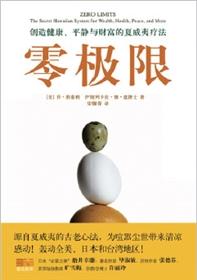不知不觉间,李佩甫的《羊的门》首版已经十六年了。
流沙般的时间,无情的岁月,使一些作品渐渐地悄无声息,也使一些作品慢慢地显豁出来。李佩甫的《羊的门》,无疑属于后一种。
十六年后,重读《羊的门》,依然让人感觉内涵丰韵,笔锋锐利。十几年以来,涉及乡土现实、乡土政治的作品纷至沓来,林林总总,但无论是从内蕴营造的浑厚上看,还是从艺术手法的老到上比,还鲜有作品能与李佩甫的《羊的门》相提并论。
在《羊的门》1999年版的封底上,印有我一小段荐语:“李佩甫的《羊的门》,很让人大喜过望。它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由人际关系的大网织构成的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和特有的国情,从而使它成为读解中国社会的重要作品。”重读《羊的门》,这样的一个总体感觉再次得到了确证与确认,并在乡土政治的明揭与暗喻上,又有不少新的感知与感悟。
地处中国腹地的中原,不只在地理位置上以其中枢性连接东西,贯通南北,而且在文化领域里以其传统的根性茹古涵今,辐射九州。就中国乡土社会和农耕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来看,由上古到唐宋形成的中原文化,一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但这份丰厚而绵长的传统文化,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吸纳了越来越混杂的内涵,表现出越来越复杂的状态,这使它带有了更加纷繁的基因,并具有向着不同方向倾斜的可能。李佩甫的《羊的门》,便是从乡土政治的特殊视角,以呼家堡为样本,来探悉当代中国农村的政治运作及其背后的文化密码。从表象上看,作品是以对当下官场生态现实的揭示,来探察传统文化的积淀与浸润;从深层上看,则是揭示传统文化对乡土生活的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以及无形中对置身其中的人们的塑形与钳制。显而易见,《羊的门》对于乡土政治这个主要的描写对象,是明揭与暗喻兼备,反思与批判并举的。
从《羊的门》两个主要人物的活动场景来看,呼国庆处于官场前台,呼天成隐于官场幕后;从他们的活动方式来看,呼国庆明火执仗,呼天成韬晦运筹,这一前一后两个人,一明一暗双重线,在相互映衬和遥相呼应中,多层面又活生生地揭现了呼家堡“人场”关系的无所不能,以及当代关系文化的高深莫测。
但从根本上说,《羊的门》只有一个主场,那就是“呼家堡”,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呼天成。而且,经由呼家堡这个主场,呼天成这个主角,作品揭示了一个乡土社会的全部隐秘,展现了有关乡土政治的所有想象。美与丑、善与恶,“神”与人,人与“畜”,在呼家堡这块土地上,在呼天成这个人物身上,都声息凝聚,自成一体,浑然“天成”,让你难以一眼洞穿,更难以一言蔽之。
不是么?!在呼家堡这块“绵羊地”,充满着“败处求生”、“小处存活”的生存本能与生活技能,呼家堡人这种超常的隐忍与天然的顺从,既令他们总能苟且偷生、安渡险境,又使呼家堡人成为呼天成营造权力场的上好土壤与绝佳舞台。面对呼天成把人当成“羊”来放牧的作为,呼家堡人从忧心、疑心,很快就过渡到忠心和诚心,甘愿成为呼天成鞭子下的温顺“绵羊”,供他差遣,任他蹂躏,并以之为荣,以此为幸。作品的最后,当人们得知发了高烧的呼天成想听狗叫时,在徐三妮跪下学狗叫之后,“全村的男女老少也跟着徐三妮学起了狗叫”,使得黑暗之中的呼家堡,“传出了一片震耳欲聋的狗叫声”。可以说,就揭示集体无意识的奴性而言,没有比这种为了主人高兴甘愿群体学狗的描写更其生动,更令人惊愕了。从一水土养一方人上说,呼家堡与呼天成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他们是彼此成就、互为因果、合而为一的文化共同体。
作为一个农村典型的缔造者、乡土政治的操弄者,呼天成其人,更是充斥了一个诸多矛盾元素纠合及复杂性格的混合体。呼天成自称是“玩泥蛋的”,但他话里有话,他其实是把乡民当成“泥蛋”,把政治当成“泥蛋”,把官员当成“泥蛋”……他把这些都视若脚下的泥蛋蛋,玩弄于股掌之间。呼天成从一个村支书成为“绵羊地”的“牧羊人”,是有一个过程的。他从起初的心里没底、心神不定,到硬着头皮试着整人,竟然每每成功,屡试不爽,遂发现胆子有多大,效果就有多好。从此,他放开胆子整治乡民,从借用孙布袋的“脸”祭旗,到利用批斗会、展览会操弄乡民,逐渐使乡民们匍匐于自己脚下,自己遂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他确实擅长于“牧人”,既把乡民们当成待宰的羔羊肆无忌惮地放牧,又常常在落难的官人、文人危困之时施以援手。“牧人”与“救人”,成为他常用的两手,而这,也确实帮助了许多落难官人起死回生,成为呼天成经营的最广泛、最重要的“人脉”资源。这一特殊的“人脉”,以官员居多,以官场为主,下起县处、厅局,上至省委书记甚至京都大员,都视他为再生恩人,可为他任意遣用。正因为呼天成有了许多这样放置于官场网络的大大小小的“棋子”,他总是胸有成竹、处乱不惊,并且总能把输棋走赢,把死棋盘活。
在呼家堡这个所谓当代新农村典型的营造过程中,呼天成专制又专注,为己也为人。他利用种种手段,借用种种机会,既令自己成了说一不二的“神主”呼伯,也使呼家堡人走出贫穷,步向小康。在他的观念世界里,封建主义的思想,小农经济的意识,江湖帮派的习性,乌托邦的理念,天主教的余音……都以一知半解和有意曲解的方式相互杂糅在一起,成为主导他行为方式的主要元素和基本要件。在这是个大杂烩式的乡村政治家身上,大雅与大俗浑然一体,大善与大恶难解难分,可以说,在当代文学堪称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里,像呼天成这样的丰繁得令人难以辨识、复杂得令人咀嚼不尽的人物形象,委实并不多见。也可以说,由于塑造出呼天成这样一个独特而奇崛的人物形象和典型性格,《羊的门》便卓具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
李佩甫是我一直很看重的当代作家,他完成《羊的门》以来,先后写出了《城的灯》、《等等灵魂》、《生命册》等长篇小说,虽然这些作品无论是内蕴考量还是艺术表现,在《羊的门》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有所出新,但我却一直偏爱《羊的门》,并固执地认为——无论是在乡土生活的深刻透视上,还是独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羊的门》都是不可替代的,别的作家不能,李佩甫自己也不能。
2015年8月13日,于北京朝内